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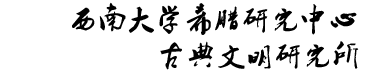
| 从《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窥探古典时期雅典的妇女地位(许鸿) |
| (发布日期: 2017-06-12 10:54:43 阅读:次) |
《古典学评论》第2辑
从《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窥探古典时期雅典的妇女地位
许鸿
摘要:古典妇女研究是近四十年来古典学界致力于恢复古代社会全貌的新课题。《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是阿提卡演说词中的杰作,里面包含许多雅典家庭生活的细节, 更重要是的是它涉及对通奸罪的处罚。该演说词深刻地揭露出古典时期雅典社会男尊女卑的生活状况。
关键词: 雅典 女性地位 名字 家庭 通奸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古典时期的妇女研究兴趣萧然。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古典学者主要将古典时期的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为研究之重,另一方面是由于相对于较为丰富且系统的军事政治文献,古典时期记录妇女的文献实在稀少而且分散。1975年学者萨拉·博美罗伊(Sarah B. Pomeroy)的《女神,妓女,妻子以及女奴, 古典时期的妇女 》[1]横空出世,被誉为第一部英语世界关于古典妇女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妇女状况进行调查,系统地展示了从荷马时期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约1500年的古代妇女社会史研究。妇女研究领域的开拓,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的新主张。他们主张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强调被传统史学忽略的细微声音,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范围,要求对历史进行包括社会和经济的全面研究。[2] 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学者对古典妇女的研究蔚然成风,性别在政治组织原则中的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探讨,近几十年以来很多成果陆续问世。 迄今为止,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妇女在公共领域的职责、家庭生活以及古典法律规定等问题的研究,普遍认为女性在古典社会的地位十分低下。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侧重于整理文献资料,将不同时间和地域中分散的文献综合起来进行专题研究。裔昭印在研究古典时期的妇女问题时,便是沿袭此种方法,很好地呈现出古典雅典妇女的家庭和私人生活总体状况。[3] 笔者拟以《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4]为主要史料,结合其他古典文献,集中分析其中所反映的雅典妇女的实际地位。该文献为古典时期雅典演说家吕西阿斯(Lysias)演说集开篇之作。雅典公民欧菲勒托思(Euphiletos)因杀害与其妻通奸的埃拉斯托斯特尼(Erastosthnes)而被指控为犯下谋杀罪。演说家吕西阿斯为欧菲勒托思撰写的《关于埃拉斯托斯特尼》乃是对其谋杀罪之辩护词。该演说词因涉及通奸罪的处罚,因而成为学者们研究古希腊社会史、城邦法律以及妇女地位的珍贵文献。笔者拟从对女性名字的刻意隐藏、夫妻家庭生活以及对通奸罪的处罚这三个方面对该文献做一个全面的解读,并就其中所披露的古典时期雅典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略陈管见。
一 女性名字被刻意隐藏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通读吕西阿斯的《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通篇不见欧菲勒托思之妻的名字。欧菲勒托思在该演说词中至少14次提及其妻,都是以“妻子”(gune)或者“她”(ekeine)作为代称(吕西阿斯,1.6-7),却从未说出她的名字。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然而,与其妻通奸的男性的名字“埃拉斯托斯特尼”(吕西阿斯,1.4)被提及6次。此外,与本案相关的另外两位女性,一位是偷偷告诉欧菲勒托思他的妻子和埃拉斯托斯特尼通奸之事的老妇 (吕西阿斯,1.15-16), 另一位是帮助欧菲勒托思的妻子与埃拉斯托斯特尼通奸的女仆(吕西阿斯,1.18),她们的名字我们也无从得知,同样只用“女人”或者“她”来代替。与此相反,本案中另外一位在案发当天和欧菲勒托思一起共进晚餐的男性“索斯特拉图斯”,他的名字在文中则两次被提及(吕西阿斯,1.22;39)。值得注意的是,欧菲勒托思在案发当晚离家极力寻找证人,就连一个不在家的邻居“哈莫迪乌斯”(吕西阿斯,1.41), 他都有将他的名字写下。显然,与本案相关的女性名字是被作者刻意隐藏了起来。事实上,雅典女性在文献中出现的情况是十分有限的,整个古希腊的文化活动如公民集会、法庭、体育场以及其他日常男性会面场所都不对女性开放,因此在现有关于男性公共生活的文献中,女性基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列。但是女性的名字在整个古希腊文献中并没有完全被淹没,如古希腊剧作家笔下所虚构出来的许多女性人物, 欧里庇得斯笔下敢爱敢恨的美狄亚,可歌可泣的特洛伊妇女,为爱出逃的海伦等等。此外,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我们发现在当时的墓碑和祭祀文献中也有很多女性名字存世。[5] 但是在演说词中,女性的名字并不多见。 学者大卫·沙普斯(David Schaps)通过对古典时期众多文献进行研究,发现在阿提卡的演说词中避而不谈女性的名字既非一种绝对现象,也非一种偶然情况,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6] 他通过对阿提卡演说词综合分析,进一步指出,在众多演说词中只有三类女性往往被提到名字,一是名誉不好的女性,二是仇敌的妻子,三是已故的妇人。[7] 对于自己家庭中的女性,男性通常在公众场合避而不谈。即使在法庭中,男性也极力避免提到家中女性的名字,除非是在司法程序中的绝对要求,男性才提供家中妇女的名字。[8] 此种文化现象,学者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源于雅典民主派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元前431年的葬礼演说词中对女性的告诫:“为了你们自己的名誉,最好关于你们的流言不要在男性中四起,不论好坏。”(修昔底德,2.45.2)[9] 此言听起来似乎是伯利克里希望整个雅典女性从整个社会团体中抽离出来,形成雅典社会团体在文化上对女性保持沉默,是绝对男权在当时社会的体现。然而,有学者指出伯利克里之言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环境下,不得不出的战时策略。因为女性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柔弱、情绪化以及私生活的代表,她们被社会权利和公共生活排除在外。减少男性对女性的谈论,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女性对公共生活的干扰,使雅典男性公民能专注于战事。[10] 伯利克里对女性的劝诫,毋宁说是他站在整个雅典公民团体的利益上对当时雅典女性提出的一种合作要求。然而,伯利克里对雅典妇女的劝诫中流露出的偏见被某些学者扩大化,以至于认为在整个古代社会对女性态度就是在公众场合保持缄默。[11] 笔者认为吕西阿斯的《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中对欧菲勒托思的妻子、女仆以及另外一位老妇人名字的刻意隐藏,恰恰是当时雅典公众社会对女性偏见的一种反映。欧菲勒托思对这三位女性的名字的缄默,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对她们名誉的保护,或可以说,是对自己家庭荣誉维护。
二 家庭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 欧菲勒托思在《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中所描述的他与妻子的家庭生活同样从各个层面上反映出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首先,在他们结婚之初,欧菲勒托思小心“看管”(phulatto)他的妻子,尽量不让她感到不悦也不让她太过自由。当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才开始信任她,并将全部家务交由她管理(吕西阿斯,1.6)。由此看来,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新婚妻子在夫家的生活难免被怀疑和监视。根据雅典法律,雅典妇女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于雅典社会结构中,她们必须附属于某一个家庭(oikos)。此家庭往往是由一位男性作为法定监护人(kyrios)来代表和领导整个家庭。 当女孩没有结婚,她处于父亲的监护之下。当她已嫁为人妇,丈夫便取代她的父亲成为她新的监护人。当她与丈夫离婚或者丈夫过世,如果他们有儿子,儿子成为她的监护人;如果没有生育儿子,她将回到原来的监护环境下。[12] 如此严密的监管制度,实则是一个男权社会的缩影。这里面当然存在对女性保护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嫁妆”的归属问题。当某一女性嫁给某一男性之时,女方的父亲即她当时的监护人必须给女方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家具或者其他动产作为嫁妆。这笔财产当男女双方离婚之时男方必须将其原数归还女方原监护人;如果女方的嫁妆被男方动用,无力偿还,男方则每年要付高达百分之十八的利息给女方原监护人;如果女方丧偶,又没有儿子,女方和她所带的嫁妆要归还原监护人,如育有儿子,女方的嫁妆将由成年儿子或等未成年儿子成年之后继承;如果女方过世,女方的嫁妆可留在夫家由其儿子在成年之后继承,若无儿子,女方的嫁妆将归还于原监护人。[13] 雅典法律对于女性嫁妆的规定反映出当时雅典人对婚姻的观念。嫁妆作为一笔由女方家庭提供的财产,显然不是给女方的,而是随着女方监护人的转移而发生所属权转移的一种财产形式。这种规定在防止丈夫苛待妻子方面确实能对妻子起到保护作用,因为如果妻子受到丈夫非难,女方的家庭有权提出终止婚姻并要求丈夫必须返还嫁妆。此外,女方的父亲也可以单方面要求其女儿结束和现任丈夫的婚姻,如女儿和现任丈夫没能产下男孩,或者他想寻找对他整个家庭在财富和政治地位上更有帮助的新乘龙快婿。[14] 因此,这就可以解释上文中为什么欧菲勒托思在他与妻子的婚姻之初,他要小心“看管”他的妻子,对她有所防范,笔者认为因为他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财产或者说是两个雅典男性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达成的契约之上。此外,欧菲勒托思说他在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开始信任他的妻子。他在文中并没有指明是男孩还是女孩,而是用一个中性的词“小孩”(to paidios)(吕西阿斯,1.6;9-12;14) ,但是根据以上关于雅典法律对婚姻的规定,可以推断出这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也就是说她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他才开始信任她,他才以为自己的婚姻生活稳定下来。这些都有力的证明当时雅典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中详尽描述了欧菲勒托思和她妻子的居住和生活状况。欧菲勒托思家的住宅有两层,上面一层住女眷,下面一层住男性,两层房子拥有同等的居住面积。当孩子出生以后,他妻子因为哺乳和不时需要给孩子洗澡,因此她不得不来回上下楼。为了降低妻子上下楼的危险,欧菲勒托思让他的妻子搬到了楼下,自己住到了楼上(吕西阿斯,1.9)。古希腊语andron和gunaikon分别指代男性住所和女性住所,欧菲勒托思和妻子虽然同住一栋房子,但是却要分开居住,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常理。女性同男性分开居住不是欧菲勒托思家特有的,而是古典时期雅典家庭的基本生活模式,色诺芬也曾写到:“男女的的住所被一道上栓的门隔开。”[15] 虽然这两位作者都没有直接刻画女性在家庭中具体的生活细节,但可想而知,当时的女性是生活在同男性相对“隔离”的世界里。 同样这也是古代雅典社会对男女两性区别对待的又一例证。 古典学者普遍认为雅典的妇女地位太低,她们被限制在家里,与外面的公共政治以及经济生活隔绝,就连在家她们都要避免和不必要的男性碰面。[16] 但是这并不表明当时的妇女没有外出的自由。欧菲勒托思的妻子就是在婆婆葬礼上和埃拉斯托斯特尼无意相识(吕西阿斯,1.7) ;她也可以半夜去邻居家借火(吕西阿斯,1.14)。此外,她还可以去神庙参加宗教节日(吕西阿斯,1.19)。 这些表明雅典女性并不像某些古典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像是被“幽禁”在家中与外面的社会完全隔离。[17] 虽然她们在公共以及政治生活中鲜有身影,但是我们还是偶尔能看到她们在社群中发出的隐隐微光。不管怎样,男女分开居住的基本生活模式再一次表明女子在家庭中卑微的地位。 最后,该演说词中认为男人纳妾,拥有情人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受法律保护(吕西阿斯,1.31)。德摩斯梯尼也说过:“情人为我们提供欢乐,妾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妻子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嗣而且是我们家产最忠诚的守护者。”[18] 情人和妾通常来自于奴隶或外邦人,还很有可能是城邦中穷苦的自由人家的姑娘,她们由于家庭不能负担嫁妆而不得不去做别人的情人和妾。[19] 一般来说,情人和妾有单独的住所,但是某些情况下她们会跟男子的合法妻子一同生活在一起,一同受男子“监护”。她们跟合法妻子一样,是男子家庭成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雅典法律规定,情人和妾所生的孩子不享有公民权,也没有继承男性土地资产的权利。[20] 她们不允许跟除该男子以外的人发生关系,否则将以通奸罪论处。情人和妾的身份低于合法妻子,加上她们没有相应的“嫁妆”进入夫家,她们的待遇很多时候不如妻子。如在《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中欧菲勒托思可以和他家的女仆任意发生关系(吕西阿斯,1.12),当他需要查明他妻子和别的男人奸情之时,他对女仆暴力相逼甚至动用私刑(吕西阿斯,1.18)。 这些都表明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女仆根本不受法律保护。
三 通奸罪重于强奸罪 吕西阿斯的《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中最让人瞠目结舌的观念是根据雅典法律通奸罪要比强奸罪严重很多。如果丈夫捉奸妻子和别的男人在床,丈夫有权杀死通奸者,这条法律同样适用于丈夫的情人和妾,而且丈夫的行为不构成杀人罪(吕西阿斯,1.30-31)。此外,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词中同样提供了可当场杀死通奸犯的相关证据:“如果一个人在运动赛场上无意地导致另外一人死亡,或在战争中杀死别人,或者他当场杀死与他妻子,母亲,女儿,姐妹以及情人通奸者,他都不应受到流放,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德摩斯梯尼,23.53)[21] 德摩斯梯尼的这段话也被古典学者当作最有力的“雅典通奸法令”, 而且有学者指出欧菲勒托思在该演说词中所依据的法律就是上文德摩斯梯尼之言。[22] 相对于通奸犯,强奸犯的处罚则要轻得多。如果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自由男性或者是小孩,那么他将被处以双倍罚金。如果他强奸一个女人,只要不是通奸,同样也只需要付双倍的罚金(吕西阿斯,1.32)。通奸犯所受的处罚是死刑,而强奸犯只需要付罚金。为什么会如此?欧菲勒托思对此有所解释:强奸犯使用暴力对他人侵害,违背他人意志,会被受害人憎恨;相反,通奸犯用引诱的方式,侵蚀的是他人的灵魂,导致别人的妻子跟他们比跟自己的丈夫更亲密。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别人的财产,混淆他人的子嗣。因此立法者将通奸罪定为死罪(吕西阿斯1.33)。 对于欧菲勒托思的解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通奸者通过对他人妻子的引诱破坏了妻子和丈夫的婚姻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和信任被摧毁。而这种爱和信任关系的破裂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欧菲勒托思最不能容忍的第二个问题,即妻子作为他整个家庭财产的守卫者以及他合法子嗣的孕育者,她与别人通奸将很有可能导致他自己家庭财产的损失,别人的孩子会成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学者凯里(C. Carey)分析认为当时希腊社会认为婚姻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给男方寻找灵魂伴侣,而是给他的家庭诞生出合法的继承人。正式的婚姻安排往往体现了这一点,首要考虑就是要求妻子能为自己生育合法继承人。[23] 从上文对嫁妆归属的分析就能得知男性合法继承人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而这也成为男女结为夫妻最重要的责任。当时的社会尤其强调血统的纯正性,在维护家族血统性方面,强奸对其的威胁在某种程度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停止和受害人发生性行为,就可以得知强奸是否导致受害人怀孕。如果怀孕,可以采用流产或者遗弃的方式来保护家族的血统纯正。但是通奸带来的麻烦要比强奸复杂得多。它的行为发生在丈夫不知晓的情况下, 因此他们无法知道妻子到底怀了别人孩子还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清楚已出生的孩子的身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通奸罪的处罚要比强奸罪严重得多,且欧菲勒托思执意要怒杀与其妻通奸者时的缘由和动机。 综上所述,《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中所披露的雅典的通奸法显然是站在保护家庭的立场上,维护的是男子的财产和荣誉,对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却只字未提,而这种中立的态度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从未严肃对待女性在社会中的行为而造成的。如他们对女性名字在公开场合的的缄默,男性对女性的监护,男女在家庭生活分居,以及男人可以变相多妻等等。这些都表明古典时期的雅典是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女性在公共活动和家庭中不仅地位卑微,而且不受法律保护。 (作者:许鸿,1990——,都柏林大学古典系博士生,主要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史)
[1] 萨拉·博美罗伊:《女神,妓女,妻子以及女奴,古典时期的妇女》(Pomeroy, B. S. Goddnes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 说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 1975年版。 [2] 科恩等主编:《剑桥古希腊法律指南》(Cohen, D & Gagarin, 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年版,第236页 [3] 裔昭印:《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历史研究》2000年02期。 [4] 《吕西阿斯》(Lysias ,I,“On the Murder of Erastosthnes”,英译者Lamb, W.R.M. ),《洛布古典丛书》( Loeb Classical Library),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年希腊文英文对照版,第2-27页。本文所引用的《关于谋杀埃拉斯托斯特尼》皆根据古希腊原文。 [5] 参见麦克拉兰:《古希腊妇女史料汇编》(MacLachlan, B.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A Sources Book) , 连续国际出版社(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2年版,第115-130页。 [6] 沙普斯:《女性很少被提起:礼节与女性的名字》(Schaps, D. “ The Women Least Mentioned: Etiquette and Women’s Names” ), 《古典学季刊》(The Classical Quarterly) , 第27卷, 1977年第2期,第323 页。 [7] 沙普斯:《女性很少被提起:礼节与女性的名字》,第 328 页。 [8] 沙普斯:《女性很少被提起:礼节与女性的名字》,第339 页。 [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Smith, C.F. trans.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洛布古典丛书 (Loeb Classical Library),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年版 [10] 蒂勒尔和班尼特:《修昔底德,2.45.2;伯利克里关闭女性声音》(Tyrrell, Wm. B. and Bennett, L.J. “Pericles' Muting of Women's Voices in Thuc. 2.45.2” ) , 《古典杂志》(The Classical Journal), 第95卷, 1995年第1期,第 38-39 页。 [11] 有学者指出伯利克里所提倡的尽量少的在公众面前表扬或是责备女性,发展到罗马时代变成为妇女最大的荣誉就是从不被人提起。参见坎塔雷利:《古代希腊罗马妇女角色与地位》(Cantarell,E. The Role and Status Women in Greek and Roman ) , 巴尔的摩出版社 (Baltimore, Md.) 1981年版,第126 页。 [12] 布伦德尔:《古希腊妇女》,(Blundell, S.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年版, 第114页。 Blundell, S.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14. [13] 布伦德尔:《古希腊妇女》, 第115-116 页。 [14] 布伦德尔:《古希腊妇女》,第 116 页。 [15] 参见色诺芬:《家政论》(Xenophon: Oeconomicus,9.5. Machant, E.C.etc trans.), 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年版。 [16] 怕德尔:《古代妇女的形象》(Padel, R. in A. Cameron and A. Kuhrt eds. Images of Women in Antiquity ), 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3年版, 第3-19 页。 [17] 参见科恩:《隔离,分离,古典时期雅典妇女地位》(Cohen, D. “Seclusion, Separation,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lassical Athens”) ,《希腊与罗马》(Greece & Rome) ,第36卷,1989年第1期, 第3-15 页; 另见沃尔珀特:《吕西阿斯第一篇与家庭政治》(Wolpert, A. “ Lysias 1 and the politics of Oikos”), 《古典杂志》( the Classical Journal) ,第96卷, 2001年第4期, 第415-424 页。 [18] 德摩斯梯尼, 59, 122: τ?? μ?ν γ?ρ ?τα?ρα? ?δον?? ?νεκ? ?χομεν, τ?? δ? παλλακ?? τ?? καθ? ?μ?ραν θεραπε?α? το? σ?ματο?, τ?? δ? γυνα?κα? το? παιδοποιε?σθαι γνησ?ω? κα? τ?ν ?νδον φ?λακα πιστ?ν ?χειν. 参见博斯 译:《德摩斯梯尼,演讲词之50-59篇》(Bers, V.: Demosthenes, Speeches 50-59) , 古典希腊演说集第6卷 (The Ora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V. 6),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3年版,第191-192页。 [19] 布伦德尔:《古希腊妇女》(Blundell, S.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年版, 第124 页。 [20] 布伦德尔:《古希腊妇女》,第125 页。 [21] 参见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 III ,Vince, J.H trans.) , 洛布古典丛书,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35年版,第248-249页。 [22] 科恩:《法律、性与社会:古典时期雅典的道德执行》(Cohen, D. Law, Sexuality and Society: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in Classical Athens),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年版,第101-106 页。 [23] 凯里:《雅典法律中的强奸与通奸》(Carey, C. “ Rape and Adultery in Athenian Law”) , 《古典学季刊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第45卷, 1995年第2期,第415 页。 |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