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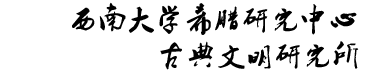
| 王志超译:雅典民主的传统:公元1750年——1990年 |
| (发布日期: 2017-07-08 16:37:07 阅读:次) |
《古典学评论》第3辑 雅典民主的传统:公元1750年——1990年[1]
摩根斯·赫尔曼·汉森 著 王志超 译
到1994年为止,从克里斯提尼(公元前507年)[2]向雅典引入民主政体之时算起,已经过去了2500年;到那时,这个周年无疑将会得到所有自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的庆祝,而这个名词实际上涵盖了西方世界的所有国家。但是,在庆祝期间,质疑者们至少会问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首先,雅典的“民主”(demokratia)与现代“民主”(democracy)有多少共同点?其次,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回顾和反思古代民主模式而得以形成的?雅典不仅是希腊的学校——正如伯里克利在他的葬礼演说中说的那样[3]——而且也是在今日西方世界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学校吗?或者,换一种问法,雅典的范例只是构成现代民主的巨大拼图中的一小块吗,甚或只是相当不重要的一块,属于那些除了上面的天空和海洋什么提示都没有的不明板块,因而难以放置到正确的位置吗?
我将会通过比较现代民主的标准定义与雅典民主的古代记述来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第15版中,“democracy”条目的开头内容如下:[4]
民主是一种基于人民自治、在当代主要是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机构与向人民负责的行政机构的政府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基于人人平等以及他们在生存、自由(包括思想与表达的自由)与追求幸福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等基本前提的生活方式。
通过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修昔底德给出了下面这个关于雅典民主的著名定义:[5]
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政治(demokratia),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6]解决私人争端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pasi to ison);在政府事务中,人们是轮流担任官职的,凭借身份获得官职的是少数,[7]但是对于有才能的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即便贫穷,也不会因为身份而受到阻碍。自由是我们的公共生活的特征;即使是平时私人交往中互相猜疑,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肆意放言,讲了一些刺耳但无害的不同意见而发怒。
在我看来,这两段材料实际上表明,雅典民主与现代自由主义民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就像古代的demokratia一样,现代的democracy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观念;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一种民治(尽管是通过代表来统治,而非公民们通过公民大会进行直接统治);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它与自由和平等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公域与私域的严格区分。
关于demokratia与democracy的详细比较,可以参见我的论文《雅典是Democracy吗?》;[8]在这儿,我将解答我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代自由民主与古代雅典民主会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呢?很多古典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治思想家偏爱的解释是:现代民主观念得到了浓厚的古典传统的激发与塑造,如果没有古典传统,尤其是雅典民主观念的影响,近现代民主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古典传统对18世纪下半期的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最大。所以,这些相信现代民主起源于古典时代的学者们都强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意义,认为正是通过这两次历史事件,古代的demokratia在现代的democracy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烙印。[9]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中,阿伦特分析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思想背景,写道:“若没有古典时代的样板……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者们就不会拥有为前人所不敢为的勇气了”。[10]不过,“古典时代的样板”是一个内涵很大的词汇,基本覆盖了希腊罗马文明的所有方面。作为古典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雅典民主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大西洋两岸的革命并为现代民主铺平了道路呢?
希腊民主VS雅典民主
论及古代民主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时,一个很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泛指的“希腊民主”传统与个案意义上的“雅典民主”传统之间的不同。在约1200年到约1800年之间的政治思想著作提到古代民主的时候,几乎都是来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柏拉图对话录(《政治家》(Statesman)《理想国》(Republic)第8-9卷)与波里比乌斯(Polybius, Book 6)对民主的记述。
在这些作品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波里比乌斯讨论了泛指意义上的民主,只有少数地方提到了雅典民主。虽然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是古典时代希腊的很多实行民主政制的城邦的典范,[11]但是,雅典是一个规模超常的城邦,拥有很多其他城邦所没有的制度;[12]而且,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民主是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中实行最为普遍的政体形式。[13]柏拉图在其早期的对话录中明确地提到了雅典民主,例如《哥尔吉亚篇》(Gorgias),[14]在《法律篇》(Laws)中也在很多地方间接讨论了雅典的制度,[15]但是,在《理想国》与《政治家》中,讨论民主政体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雅典,只有一处地方隐晦地提到了苏格拉底审判。[16]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引用了大约300个历史实例,与雅典有关的不超过30个,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与公元前6世纪的庇希特拉图僭主政治和公元前411年与前404年的寡头政变有关。唯一一处详细讨论雅典民主的地方是在第2卷中讨论了梭伦式的混合民主,[17]其他地方只提到了陶片放逐法、克里斯提尼对外邦人的归化以及另外一些具体制度。当讨论民主时,提到雅典的地方远远少于昔兰尼、叙拉古、罗德岛、科斯和其他城市。因而,依笔者之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在结合了众多城邦材料的同时,又忽视了雅典民主很多典型制度的基础上而对民主进行批判的。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敌视民众统治的态度。民主总是被视为是穷人或暴民(社会意义上的demos)的统治,而非全体人民的统治,这就是雅典民主派对demos与demokratia的理解。[18]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波里比乌斯对雅典民主没有任何兴趣,一句话就带过了。[19]
不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将民主视作政体的三种基本类型之一,这种观点反映在从1250年[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复原到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兴起之间出现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在这500多年中,关于古希腊民主的标准定义包括下列7个要点:
1. 民主不是单独出现,而仅仅是政体的三种基本类型之一: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 2. 这种叙述是理论的而非历史的。作为一种多数人统治的政体,民主仅仅是作为一种不需要人们过多注意的政体形式顺便提到的。 3. 对民主的看法大部分都是消极的,如果有积极看法,也被认为是无法实行的。 4. 大部分人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某种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要素的混合政体。 5. 当民主能够被接受时,它只是混合政体中的要素之一,而非一种单纯的政体。 6. 偶尔提到雅典政体,大多也是指著名立法者梭伦,人们相信他是温和的混合民主政体之父。 7. 上述关于古代民主的看法主要依据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波里比乌斯的作品。当涉及到雅典民主的时候,主要材料是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例如梭伦、伯里克利、德摩斯梯尼、福吉翁以及其他一些雅典政治家的传记。
请允许我通过一个例子来阐明上述7点。1756年,法国政治思想家路易·博丹(Louis Bodin)写道:[21]
政体或国家有三种类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当主权归之于一个人、其余人仅需遵从一人,就是君主制。当所有人民或者多数人民集体行使主权,就是民主制或者平民政府。当少数人集体享有主权并将法律强加于其余人,就是贵族制。所有古代人都认为国家至少有三种类型。有人还增添了第四种,即其他三种政体结合起来的混合政体。柏拉图也增添了第四种,即智者统治。但是,公正地说,这只是纯粹的贵族制形式。他不能接受混合政体作为第四种类型。亚里士多德既接受了柏拉图的第四种政体,也接受了混合政体,政体就有了5种类型。波里比乌斯辨别出了7种类型,三种好政体,三种坏政体,还有一种由三种好政体结合而成的混合政体。
然后,博丹又陆续提到了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与西塞罗(Cicero),再后,当他简要讨论民主的时候,梭伦是他提到的唯一一个希腊政治家。
将民主作为三种政体形式之一而进行大而化之的描述,还见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22]帕多瓦的马尔西留斯(Marsilius of Padua)、[23]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24]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25]约翰·洛克(John Locke)、[26]布拉克斯顿(Blackstone)、[27]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28]及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所以,将雅典民主传统视作18世纪革命者思想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有误导性的说法。
启发美国法国革命者以及英国激进派的古典样板是罗马而非希腊。[29]因而,在1787年,在费城开会的国父们创建的议会是“Senate”(元老院)而非“Council Areopagus”(战神山议事会)。在法国,西哀耶斯设计的1799年宪法中,执掌权力的是三执政官制(triumvirate of consuls)而非“将军委员会”(board of strategoi)。
当提到古希腊的政治传统时,样板也是斯巴达而非雅典。[30]甚至到了1819年的时候,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De la liberté des anciens comparée à celle des modernes)中仍然将斯巴达人的政治自由概念视作古希腊的代表性看法,[31]而雅典人的eleutheria(自由)概念却被视作例外而遭到冷遇。[32]
当偶尔将雅典当成样板时,赞扬几乎都给了梭伦式的混合民主。1787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写了一篇文章为美国的新宪法辩护,其中有20页在谈论雅典民主。[33]这是极为不寻常的现象,此前很少有人花这么多篇幅谈论雅典民主,但与此前的论著相同的是,亚当斯谈论的主要是梭伦的民主,而非现代学者们熟知的从克里斯提尼到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与之相似,在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34]德若古(de Joucourt)在狄德罗(Diderot)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35]中都将梭伦看做雅典民主的创立者,而根本没有提过伯里克利。相反,当不得不提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时,也只是作为过度民主的典型来警告那些支持大众民主的人们。结果,正如卢梭所言,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实行的不再是民主,而是一种由“智者与演说家”(savans et orateurs)主导的残暴贵族政治。[36]但是,革命者们所了解的梭伦式民主是一种历史神话,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普鲁塔克的《梭伦传》(Plutarch’s Solon)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37]的第二卷。亚里士多德的误导与普鲁塔克的歪曲使得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古典时代的雅典存在着普遍的无知与误解。
当时,唯一的例外是德国。相比于古罗马,德国人更喜欢古希腊;相比于斯巴达,德国人更偏爱雅典。而且,他们喜欢的雅典并非梭伦时代的雅典,而是拥有自由与民主的古典时代的雅典。德国人的这种传统从18世纪中期的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时代持续到了19世纪初的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时代。温克尔曼认为,雅典正是受益于自由民主的政体,才有了举世无双的艺术,[38]而在1807年,受到德摩斯梯尼启发的洪堡甚至打算模仿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写一部《自由希腊衰亡史》(Geschichte des Verfalls und Unterganges der griechischen Freistaaten)。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残篇来看,该书的主题就是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首先得到重视的个人自由。[39]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湮没在了普鲁士的保守洪流中;在1848年的革命浪潮中,虽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很快再次被俾斯麦与保守派所绞杀。所以,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反,德国此后对古典传统的兴趣从雅典转向了斯巴达;他们推崇以斯巴达法律与秩序为标志的多利亚种族,贬低曾经向往过的雅典人的自由与平等。[40]
但是,在19世纪的美国、英国与法国,人们关注的焦点却从斯巴达转向雅典,从梭伦转向伯里克利,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与法国人都表达了他们对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的赞赏。与他们相反,德国人却同样自得地将他们自己等同于率领陆上同盟与伯里克利的雅典领导的海上同盟进行战斗的斯巴达,或等同于正在与律师德摩斯梯尼领导下的民主雅典进行战斗的腓力二世领导下的马其顿。
有若干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1915年,所有的伦敦巴士都挂上了同样的海报,上面写有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对自由的赞美。[41]1920年,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退出政坛之后,将晚年岁月全部用在了著书立说上面,其中包括主张抵抗马其顿帝国主义捍卫雅典自由的德摩斯梯尼的传记。[42]然而,在德国,赫尔曼·狄尔斯(Hermann Diels)在1916年就预言斯巴达的nomos(德国)将再一次击败雅典的physis(英国与法国);即便是在战败后,德国人也没有放弃对斯巴达的向往,这反映在学校的课本中频繁引用西蒙尼德斯为李奥尼达斯及其部下写的著名墓志铭以及弗雷德里希·席勒(Fr. Schiller)的同样有名的译文:过客啊,请告诉斯巴达人……(Wanderer, kommst du nach Sparta….)。[43]德国人也钦佩马其顿人。1916年,恩格尔布雷希特·德雷鲁普(Engelbrecht Drerup)将凯瑟·威廉(Kaiser Wilhelm)视作击败了律师德摩斯梯尼(劳合·乔治)的腓力二世。[44]
在19世纪,对雅典民主的再次赞扬源自于历史学作为一个拥有自己方法的独立学科的兴起。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哲学完全盖过了历史学,而随着批判的历史学从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兴起,历史学又盖过了哲学。在19世纪上半期,对古代民主的历史学分析渐渐取代了哲学分析,大而化之的批判视角也逐渐让位于对雅典制度的更为实证性的研究。研究古代民主或雅典民主的主要资料也不再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换成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以及1890年后发现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伯里克利的风头压倒了梭伦,对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更为积极的描述也取代了对希腊民主的消极看法。
对雅典民主的这种全新理解可以追溯到三位重要历史学家,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一位德国人。最重要的一位是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他从1846年到1856年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卷《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45]1851年,维克多·杜鲁伊(Victor Duruy)在法国出版了《古代希腊史》(Histoire de la Grèce ancienne)。[46]在德国,恩斯特·库修斯(Ernst Curtius)也写了3卷本的《希腊史》(Griechische Gechichte),出版于1857年到1867年间。[47]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位先生不仅是伟大的学者,其他方面也很杰出。格罗特是英国下院的激进党领袖,杜鲁伊是拿破仑三世在位时的教育部长,库修斯是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私人教师,后者在1888年曾任德国皇帝。这三位顶尖的历史学家都是自由派,他们对雅典民主,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都持有积极的看法。乔治·格罗特无疑是三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受到了德国的批判史学的启发,尤其是博克(B?ckh)与尼布尔(Niebuhr);[48]在德国,尽管自从1820年以后,对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和雅典自由的赞美就不断退却,却未完全消失,并通过格罗特转移到了英美文化圈。
在过去的150多年里,由于历史学家们采用了新方法,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领域,对古代民主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局限于与亚里士多德三种政体形态有关的若干个理论意见。在叙述民主概念的历史时,古代民主常常被写的更详细了,甚至被给予了单独的章节。[49]参考书目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古代民主,而是深入到了雅典民主,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
因此,雅典民主可能曾经启发过近现代的民主支持者,但是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时间晚得多。我们的关注点必须要从18世纪转移到19世纪和20世纪。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
民主既是一套政治制度,也是一套政治理念。当然,民主的两个层次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派相信民主制度比任何政体都更能促进民主理念的发展)。但是,在分析民主的时候,将二者分开处理更为恰当。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当代民主,也适用于研究民主的历史。所以,若是从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开始分析,马上就会有两个问题:雅典有任何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在后来的世界历史中出现过吗?如果真有类似的制度,雅典确实是那些创造制度的人们模仿的对象吗?接下来,通过简短的分析,我将讨论两种类似的制度。一种是人民大会,一种是投票程序和官员抽签制度。
在雅典民主制中,毫无疑问,最具标志性的政治机构是公民大会(ekklesia),其中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权利发言或投票。数千公民定期聚会讨论已经过五百人议事会预审的政治议题。辩论之后,通过举手表决,多数票决定结果。[50]
与雅典公民大会最为相似的政治机构是瑞士的州民大会(Landsgemeinde)。它产生于公元13世纪,今日瑞士某些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机构,数千公民出席这种开放式的政治集会。参会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与投票权。所有重要事务都必须交给人民讨论,当然,它必须首先由议事会(Kantonsrat)预审,然后交付州民大会进行公开辩论,最后举手表决,多数票通过。[51]
可见,雅典公民大会与瑞士州民大会极为相似,[52]但是二者之间不存在联系。对于控制小小的林间行政区的自由州民们来说,他们在中世纪创造州民大会的初衷是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领主们,在他们的头脑中绝没有一点模仿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的想法。
另一个拥有政治决策权力的民众会议的历史范例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市镇会议。市镇会议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1632年12月,马萨诸塞的剑桥最早颁布了规定市镇会议定期举行的法律。[53]但是,市镇会议主要是起源于清教徒的集会,[54]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们在创建市镇会议时知道雅典的公民大会。
我要考察的第二项指标是选举与抽签制度。在选举和挑选官员程序的复杂性方面,能够与雅典[55]相媲美的只有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后者的复杂性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威尼斯公爵(the Doge)选举[56]与佛罗伦萨执政官(Priorate)与正义旗手(Gonfaloniere)的选举[57]。当然,其他城市也有很多类似的官员选举。这些意大利城市中实行的投票与抽签制度与古代雅典人的投票和抽签选举方式非常相似。[58]但是,这两种制度之间并没有任何前后承继的关系,从古希腊城邦到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并不存在连续的发展线条。如果有源头的话,那也是在罗马人而非希腊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投票方式与雅典人的差别非常大,[59]抽签主要是为了排序或者为像执政官(praetores)这样的官员们分配任务。[60]罗马人从未赞同过、也从未采用过希腊人抽签选举官员的民主方法。而且,进一步说,意大利城市是在13世纪就发展出了这种复杂的投票与抽签程序来选举官员,比他们重新发现古希腊文献要早的多。因此,单从时间上考虑,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投票与抽签选举制度与古代雅典政治制度的重见天日不存在任何关联。
总之,上述几个历史范例,虽然从制度安排上看极为相似,但是并未有任何证据来解释这种相似性。从这里看,雅典人的政治机构并没有在后代那里得到保持,雅典政治机构与后来的政治机构的所有相似性都是偶然的,并非出于某些前后承继的关系。
但是,如果从更宽泛和更模糊的意义上看,在作为政治制度的雅典民主与近现代民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也不是不可能的。直到1790年左右,民主仍旧意味着人民通过民众大会来统治自己的政体。代议制民主的概念首次出现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61]于1777年写的一封信里。但是,这个概念除了在18世纪最后十年短暂流行外,[62]发展非常缓慢,代表制概念嫁接到民主概念之上用去了数十年时间(这是托马斯·潘恩在《人权》一书中创造的比喻)。[63]在代议制民主旗号下发动的第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运动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28年以美国西部和南部为基地创建民主党。[64]在法国,在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的推动下逐渐接受了代议制民主的观念。但是,直到1848年,新生的瑞士联邦宪法仍然将民主与代表制作为对立的两种制度来看待。[65]
从19世纪中期起,代议制民主的概念才流行起来。从这时起,纯粹民主被称作直接民主,而如果单用“民主”一词,主要指间接民主或代议制形式的民选政体。[66]此后,讨论民主经常是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对立开始,前者已经变成了彻底的历史概念;在这种语境中,直接民主既指普遍意义上的古希腊民主制(demokratia),也具体指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67]
但是,除了这种纯粹的历史角度之外,雅典民主或者说雅典民主的现代神话还出现在当代关于理想民主的讨论中。直到1850年左右,人们仍旧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民主,大部分人都排斥民主。[68]因为它培养煽动家制造党争,而且纯粹民主在现代民族国家又是无法实行的一种制度。
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议制民主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流行。大约从1915年起,民主已经被广泛接受;人们可能会回忆起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口号:“让世界因民主变得安全”。民主成为确凿无疑的正面词汇,[69]甚至成了纯粹的口号,而根本无须再进行解释的就是:最民主的政体也是最好的政体。
然而,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直接民主比代议制民主显得更为民主,尤其是对当代很多代议制民主的支持者们来说,当前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形态并不像全体人民直接统治的直接民主政体那么民主,令人稍感忧虑。代议制民主的主要问题就是参与性的问题。在19世纪,当世界各地的民主派都在争取普选权的时候,还感觉不到这一点,但在1918年以后,当普选权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之后,民主派就不得不面对人民不愿意使用他们获得的民主权利的问题。尤其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选民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冷漠成为民主面对的主要威胁。[70]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回顾古代雅典民主并赞美古代雅典人的政治参与水平成为普遍现象。[71]
实际上,雅典民主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就是大约3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的参与水平。雅典人每年都要召开40次公民大会,出席大会的公民稳定在6000名左右。每年大约200天左右的开庭日,从年龄在30岁以上的6000名左右的公民中抽签选举出几千名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绝大部分人都至少在500人议事会中服务过一年。每年至少投票或抽签选举出700名左右的各种官员。[72]在世界历史上,这种规模的政治参与也罕有其匹。有人称赞这种参与规模,[73]也有人厌恶它,后者喜欢正确地指出政治参与权利限制在成年男性公民范围,而成年男性公民在雅典总人口中是少数[74],并且,即便在雅典,权力也是掌握在一小部分活跃的政治精英手中,他们控制着各个民主机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认为更多参与是民主必要组成部分的人们来说,雅典也是样板。古希腊人曾经做到的事情,今人也必须做到,或是通过改革代议制民主,或是通过恢复部分直接民主制度。最近,西方有所谓电视民主(Teledemocracy),通过电视民主技术,所有公民都能够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75]当人们开始讨论通过有线电视和类似的技术设备实行电子投票的时候,最常被提起的两个样板就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市镇会议[76]与古代雅典的公民大会。[77]
总之,作为政治制度的雅典民主传统在20世纪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契机是关于政治参与的广泛讨论。重建并重估了古代雅典民主制度的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学家而非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除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78]、卡梅勒·德斯穆兰(Camille Desmoulins)[79]以及其他几位思想家,雅典民主样板对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者们也没有多少影响。
作为一种观念的民主
现在,我将从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向作为一种观念的民主,并讨论民主、自由、平等之间的关系。让我通过引用近来一个关于自由民主的看法来阐明这三个概念之间在当下的关系:
民主、平等与自由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从平等与自由两角出发可以在第三个角,即民主之处连接起来,,而且通过直接连接平等与自由也形成了三角形的第三条边。[80]
与之类似,在古典希腊时期,demokratia(民主)、eleutheria(自由)与isonimia(平等)的概念也是紧密联系的。[81]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用赞赏的口气解释过这三个概念,前文已经引述过,但是伊索克拉底却表达了谴责的态度:祖先们并未实施这样的政体,它将公民们训练得认为傲慢就是民主,无法无天就是自由,胡言乱语就是平等,肆意妄为就是幸福。[82]
那么,在欧洲,在启蒙运动之后,是谁将民主与自由和平等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得三个概念构成了一套政治观念,这个概念三角是何时得以形成的?古典时期的雅典是近现代民主观念的样板吗?
自由与平等变成两种基本的政治价值主要有三个驱动力: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英国功利主义。但是,只有英国激进派与功利主义者倾向于将自由、平等与民主联系起来。三个代表性人物是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潘恩与詹姆斯·密尔。托马斯·潘恩确实称赞过古典时期的雅典,[83]他的著作证明古典传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詹姆斯·密尔关于政府的论文中,仅有一处提到了古典民主,不过却是持批评的态度。[84]如果边沁受过古希腊民主的启发,他的著作却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来。[85]而且,边沁承认,早期功利主义者赞扬民主是各自为战的,彼此并没有联系。[86]除了1800年之前的一段短暂时期,对民主的消极评价一直盛行于大西洋两岸。在美国,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20年代[87]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后才得以扭转,欧洲则持续到了1848年革命,所以,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民主的重新评价与雅典民主都没有关系。杰克逊的民主党的主要成员都是中产阶级商人,大部分都没受过多少教育,更不用说古典学了。讽刺的是,比较浓厚的古典传统主要存在于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主当中,他们更为偏爱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拥有“天然奴隶”(natural slaves)的国家,很少关心雅典民主。[88]
在欧洲,最早论述了民主-自由-平等的三角关系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89]但托克维尔很少提到古典传统,只有短短一章写了阅读古典文献的教育效果,仅此而已。[90]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本人对民主拥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相信民主可能有助于产生平等,但民主也很容易会变成自由的威胁。[91]这种状况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到了19世纪中期,民主逐渐变成为了一个积极的概念,而且与自由、平等可以共存。在法国政治思想史中,对于民主-自由-平等三者关系拥有确定无疑的积极看法的是瓦什隆(E. Vacherot)的《论民主》(Le démocratie),他在这本从1860年开始写的书中说道:“民主,一个动听的词汇,总是意味着人民自治;这是自由之下的平等。”[92]这本书出版于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作者因此还招来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
在德国,1848年革命期间,世纪之交时的政治理念民主-平等-自由(Demokratie-Gleichheit-Freiheit)出现了短暂回春的迹象。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倒退,[93]当民主派回溯历史寻找样板的时候,他们称赞的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民主层面,[94]或者甚至称赞古罗马作家塔西佗[95]简单描述过而且后来的孟德斯鸠[96]也提到过的“日耳曼人的民主”(Die germanische Urdemokratie),而雅典民主则很少受到注意。
在英国,首先将民主-自由-平等三个概念并列起来的是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97]然后是约翰·密尔关于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论文;但是,密尔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相信古代政治自由与现代的个人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98]因而,乔治·格罗特认为个人自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的首要特征的观点,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未得到广泛认可,后来他的作品就被傅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的作品《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压了下去,后者提出了古希腊罗马人不了解个人自由的错误观点。[99]
结论
在18世纪,古典传统是塑造公众思想的有力因素,但在其中鲜见雅典民主的身影。提到古代民主,人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曾经批判过的暴民政治。如果偶尔提到雅典民主,也只是梭伦式的混合民主,主要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与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到了19世纪,当对希腊民主的批判被对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民主的赞扬所取代的时候,古代民主的传统也影响很小,远远不及革命时期。雅典民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democratia-eleutheria-isonimia)与近现代民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democracy-liberty-equality)并无直接的承继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过高地评价所谓的“传统”,更不能低估人类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类似的但基本没有关系的制度与思想的能力。例如,在直接民主制度以及由议事机构召集全体人民大会方面,雅典的公民大会(ekklesia)与中世纪瑞士的州民大会(Landzgemeinde)极为相似,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另外,民主政治思想的研究也表明,雅典民主价值与19、20世纪的自由民主价值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在这二者之间,前者确实对后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产生的很晚。与其他因素相比,雅典民主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译者简介:王志超,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明史。 [1]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Tradition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A.D. 1750-1990”,原载Greece & Rome, Second Series, Vol. 39, No. 1 (Apr., 1992), pp. 14-30. [2] A. Andrewes, ‘Kleisthenes’ Reform Bill’, CQ 27(1977), 246-7; M. Ostwald, ‘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Kleisthenes’, CAH IV(1988), pp. 306-7. [3] Thuc. 2.4.1.1. [4]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th edn. (1955), vol. 7 p.182. [5] Thuc. 2.37.1-3. [6] Cf. Thuc. 5.81.2, 8.38.3, 8.53.3, 8.89.2. [7] Cf. 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II (Oxford 1956), p.108. [8] M. H. Hansen, Was Athens a Democracy? Popular Rule,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Ancient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Det 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 Historisk-Filosofiske Meddelelser 59(1989). [9] Cf., e.g., J. Rufus Fears in his ‘Preface’ to W. R. Connor, M. H. Hansen, K. A. Raaflaub, and B. S. Strauss, 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 (Copenhagen, 1990), pp.4-5. [10] On Revolution (1963, Peclican edn 1973), p.196. [11] Thuc. 2.37.1, 3.82.1; Arist. Pol. 1307b23-24; Meiggs and Lewis, 40. [12] H. J. Gehrke, Jenseits von Athen und Sparta (Munich, 1986). [13] Arist. Pol. 1286b20-22, 1291b7-13, 1296a22-23, 1301b39-40. [14] Gra. 515C-519A. [15] A. H. Chase, ‘The Influence of Athenian Institutions upon the Laws of Plato’, HSCP 44(1933), 131-92. [16] Pol. 299B-C. [17] Pol. 1273b35-74a21. [18]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1991), pp.69, 125, 301. [19] Polyb. 6. 43. [20] On the revival of Arist. Pol. with Wilhelm of Moerbeke’s Latin version c. 1250, cf. J. Aubonnet in the Budé edn. Vol. I (1968), pp. cxlviiff. [21]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6), 2.1, 7 here quoted from Tooley’s translation (Oxford, 1951), pp. 51-52. [22] De Regimine Principum 16. [23] Defensor Pacis 1.8.2-3. [24] Discorsi 1.2.3-4, 11-12. [25] De Cive 7.1, 5-7. [26]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132. [27] Commentaries 1.2.7. [28] ‘Government’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820), pp.3-5. [29] M. Reinhold,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n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Western Thought A. D. 1650-1870, ed. R. R. Bolgar (Cambridge, 1979), pp.225, 233, and passim. [30] E.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Oxford, 1969), pp.268-300; Reinhold (n. 28), pp.228 et alibi. [31] Reprinted in M. Gaucher, De la liberté chez les modernes: écrits politiques (Paris, 1980), pp.494-5, 500, 509. [32] Ibid. pp.496, 500 with note 14. Cf. also his De l’esprit de conquête et de l’usurpation (1814), II.6 and 7. [33]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7-8) in Works (Boston, 1851), IV. 472-92. [34] De l’esprit des lois (edn. Garnier Paris, 1967), I.12-15, 25, 48-49, 52, 54, 122; II. 107, 282. [35] ‘Démocratie’, Encyclopedie IV (1754), 816-18. [36]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in Oeuvres III (Pléiade edn. Paris, 1967), 10, 12, 56, (lettres) 68, 81;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ibid.), 246. [37] Pol. 1273b35-74a21. [38]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1.4 (130-3). [39] Fragments in Werke in fünf B?nden (1981), II. 74, 77, 84. [40] Carl Otfried Müller, Die Dorier (1824). [41] Cf. F. M. Turner, 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1981), p. 187. [42] Démosthène (Paris, 1924). [43] ‘Ein antikes System des Naturrechts’, Internationale Monat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 11 (1916-17), 82-102; E. Neustadt and G. R?hm, Geschichte des Altermus (1924); W. Hack, Geschichte der Griechen und R?mer (1930). Cf. the famous short story by Heinrich B?ll, ‘Wanderer, kommst du nach Spa…’ (1950). [44] 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 (Paderborn, 1916), pp.1-4: ‘Advokaten gegen K?nige.’ [45] On Periklean Athens see Vol. 6 (1848), Part 2, Chapters 46-48, especially pp.176-84 with a long quotation from Perikles’ funeral oration and Grote’s praise of Athenian democracy. [46] On Periklean Athens see Vol. 2 Chapter 19. 1 (Périclès) and 3 (La Constitution athénienne), pp.145-54 and 196-214 in the 1888 edition. [47] On Periklean Athens see Vol. 2, Book 3, Chapter 3 (pp.157-280): ‘Die Friedensjahre’. [48] History of Greece I. preface xvi; J. S. Mill, review of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VIII, Edinburgh Review Oct. 1853, 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9 (Toronto, 1978), pp.323, 328. [49] Cf., e.g., G. Sartori, Democratic Theory (Westport, 1962), pp.250-77; 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1987), pp.13-35. [50] Arist. Ath. Pol. 43-44. [51] M. Kellenberger, Die Landsgemeinden der Schweizerischen Kantone (Winterthur, 1965). [52] Hansen, ‘The Athenian Ecclesia and the Swiss Landsgemeinde’, The Athenian Ecclesia: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76-83 (Copenhagen, 1983), pp.207-26. [53] J. F. Sly, Town Government in Massachusetts 1620-1930 (Cambridge, Mass., 1930) [54] S. H. Stout, The New England Soul (Oxford, 1986), p.22. [55] Hansen (n. 17), pp.197-9, 230-5. [56] R. Finlay,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 (London, 1980), pp.141-2. [57] J. M. Najemy, 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1280-1400 (Chapel Hill, 1982). [58] Compare, for example, the voting procedure in the Athenian 5th-century courts, described by A. Boegehold in Hesperia 32 (1963), 367-8, with the procedure described in D. Waley, 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 (London, 1969), pp.30-31. [59] L.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Ann Arbor, 1966), pp. 34-58. [60] V. Ehrenberg, ‘Losung’, RE XIII.2 (1927), 1493-1504. [61] Letter 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Gouverneur Morris of May 19th, 1777. [62] R. R. Palmer,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Word “Democracy” 1789-99’,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8 (1953), 203-26. [63] Rights of Man, ed. B. Kuklick (Cambridge, 1989), p.170. [64] J. Roper,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Anglo-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9). [65] Consitution de la Confédration Suisse du 12 Septembre 1848. [66] Cf. de Toqueville’s report of 15th Jan. 1848 on the subject of M. Cherbuliez’ book entitled On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 printed as Appendix II in J. P. Mayer’s edition of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New York, 1966), p.740. [67] Cf., e.g., the entry ‘Democracy’ in the 11th edn.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III (1910), pp.1-2 and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icences (1968), pp.112-21. [68] Even as late as 1847 George Grote could still write in his History of Greece IV.346: ‘Democracy happens to be unpalatable to most modern readers.’ [69] B. Holden,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London, 1974), p.2. [70] Holden (n.68), pp.140-6. [71] B. Campbell, ‘Paradigms lost: Classical Athenian Politics in Modern Myth’,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0 (1989), 189-213; 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New Brunswick, N.J., 2nd ed. 1985), pp.33-37. [72] Hansen (n.17), p.313. [73] J. S.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 p.197. [74] J.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1776), 2.34 with note 2. [75] F. Chr. Arterton, Teledemocracy: Can Technology protect Democracy? (Washington, 1987). [76] B. J.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for a New Age (Berkeley, 1984), pp.239-40, 268, 272, 273-8. [77] I. McLean, Democracy and New Technology (Cambridge, 1989), pp.157-61. [78] Rights of Man (n.62), p.170. [79] H. T. Parker, The Cult of Antiqu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 (Chicago, 1937), p.76 with n.7 et alibi. [80] B. Holden, Understanding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1988), p.28. [81] Arist. Pol. 1310a28-33. Hansen (n.7), pp.3, 25-28. [82] Isok. 7.20. [83] Above n.77. [84] An Essay on Government (1820), ed. C. V. Shields (New York, 1955), p.55. [85] H. O. Pappé,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Athenian Democracy’, in Bolgar (n.28), p.296. [86] Plan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1817) in The Works of Bentham 10 (London, 1839), p.438: ‘This bugbear word democracy.’ [87] R. L. Hanson, ‘Democracy’, in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ed. T. Ball, J. Farr, and R. L. Hanson (Cambridge, 1989), pp.78-9. [88] E.g., John C. Calhoun and George Fitzhugh. The only intellectual who focused on Athens was, apparently, Hugh Swinton Legare: cf. W. W. Briggs, Jr., ‘Classical Influence in the Sothern Response to the Constitution’, unpublished paper read in Boston in Sept. 1989. [89]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Vol. 2, Part 2, Chapter 1. [90] Ibid. Vol. 2, Part 1, Chapter 15: ‘Pourquoi 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et laine est particulièrement utile dans les sociétés démocratiques.’ [91] The title of Vol. 2, Part 1, Chapter 2 is: ‘Pourquoi les peoples démocratiques montrent un amour plus ardent et pulus durable pour l’égalité que pour la liberté.’ [92] La démocratie (Paris, 1860), p. 7 [=de Tocqueville, 2.2.1, but without the modifications]. [93] W. Conze, ‘Demokrat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 (Stuttgart, 1972), pp.885-6. [94] 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Leipzig, 1853). [95] Germania 11. [96] Montesquieu (n.33), 1.170. [97] History of Greece IV.345; VI.180. [98] On Liberty (1859), Chapter 1 (pp.19-20 in the Prometheus Books edn.) [99] La cité antique (Paris, 1864), 3.7. |
 首页
首页